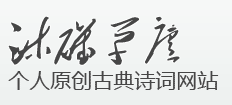来自网络 写于 2012年08月05日 02:14:33 浏览次数:7383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诗写了什么 专家称是宗教诗
核心提示: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解读那些被“错译”了的“仓央嘉措情诗”,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的诗歌中其实蕴含着许多宗教的含义。这不禁令人大失所望。

本文摘自《仓央嘉措》,作者是:任乐乐 李叶倩,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和尚,这个汉字里面最古板、最枯燥的词汇,一向只与青灯古佛为伴,一向只与寡言薄欲相行。乍看此词,空旷森严的庙宇突然闯入心中,日复一日的苦修之景不由得让人头皮发紧。
历史上诸多著名的和尚,如达摩祖师,六祖惠能,唐玄奘等,给人留下的,也无非是一段段与政治,或是宗教有关的厚重教典,叫人读来口干舌燥,心生烦闷。大概是我此生与佛无缘,和尚一词,实在不能让我提起多大兴趣。
然,自那夜在玛吉阿米酒吧偶遇“仓央嘉措”,“和尚”一词又重入我眼。那一夜,目光所到之处,却满是“浓浓的爱意”,“无可比拟的才情”,“神秘的雪域之王”……
和尚,也会有如此丰富多彩的一生吗?和尚,也会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爱情吗?或许,对仓央嘉措来说,和尚,只是他众多身份中的一个名词,在这个名词之下,涌动着数不尽的才华,情愫,还有悲惨的身世。
仓央嘉措,这位全西藏曾经最重要的宗教领袖——圣域之王,雪域高原最神秘的诗人,最多情的佛陀子弟……在这众多的头衔之下,你无法想象,他的诗作,比他的地位更令人神往,他的经历,则比他的诗作更加传奇。
历史的尘嚣已消逝了三百年,而他的一生,却至今还是众人茶余饭后的话题。然而,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一个舒适的王者,或是一个令人倾慕的才子,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历经了所有人无法想象的光荣与屈辱,承载了世间俗人无法理解的圣洁与晦暗。
仓央嘉措,他具有达赖和情郎的双重角色,又在格鲁派对抗和硕特蒙古的政治斗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一言一行足以牵一发动全身,甚至影响整个西藏的政治格局。
然而,让人疑惑的是,他是雪域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却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实权;他的佛法被藏传佛教高僧赋予极高的评价,却又被人怀疑根本不是“灵童转世”;他的身份有如雪域的莲花一般圣洁,他本人却又被传出在数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绯闻。
这些铁铮铮的事实,让人不得不对仓央嘉措提出种种质疑。
“六世达赖”,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神圣的名号?“仓央嘉措”,这又究竟是一个怎样纠结的名字?
他是圣僧?还是情种?还只是政教合一的傀儡?真实的仓央嘉措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在他的人生中,又还藏有多少谜团呢?
1.他的诗作都是情诗吗?
在时光飞逝的时空中,你可曾找到一位活佛,如他这般,权重、多情,富有传说。他轻盈地穿梭于“活佛”和“情郎”之间,他桀骜地写下流传于世的作品。他的诗歌,每一言,每一句,都似在轻轻地敲打姑娘们的心,撩动着姑娘们尚未开化的情愫。
问题是,他是活佛,他是六世达赖,他是整个西藏的精神领袖。他真的会与佛祖的教诲背道而驰,留下许多情爱诗词吗?
怀着对仓央嘉措的极大兴趣,我翻阅了无数关于他的资料。数月之后,我惊异地发现,事实似乎与传说大有出入。
仓央嘉措的诗歌,就像装在玻璃瓶底的万花筒般,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它的美丽与意义也完全不同。
传说自他消失的那天开始蔓延。人们似乎对逝去的美丽更加感兴趣,他们对仓央嘉措一生可怜的悲剧命运怀着极大的同情,并将现在流传着的仓央嘉措诗歌的版本,翻译成了许多不同的语言。
其中,似乎情诗的比例占的并不算多。更多的,是对佛祖的虔诚,是对世事的顿悟。仓央嘉措,他,果然还是佛陀的子弟。
比如说下面这段《问佛》:
我问佛:如何才能如你般睿智?
佛曰:佛是过来人,人是未来佛。
诗中只有短短一问一答,却已把人与佛的差别道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人,还是佛,仅在一念之间。
看破,人就是佛。执著,佛便是人。
我偶尔会想,当仓央嘉措写下这两句短短的话语时,他的内心可曾涌动?他的脑海会不会闪过一丝杂念?他的身世,他的处境,他的困惑,都逼迫着他在不断思考,就像一缕剪不断的麻线,紧紧压迫着他,让他无法呼吸。
周围的人,都视他为活佛,仰望他,敬重他。望着无数敬仰的目光,他将自己的心事深深埋葬,不敢说,也不能说。
我们无法揣测的是,当他的笔尖落在纸上时,佛,究竟是令他困惑的究极所在,还是他赖以逃避的避风港?
唯一让人庆幸的是,他并非一心逃避红尘的人。
在佛陀的世界里,不感受红尘,又怎能看破红尘;在佛陀的心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作为佛陀的代言人,他明白,一心只想逃避红尘的人,虽然念诵着佛经,寻找的却不是快乐自在之道,而是逃避厌世的方法。
不过,即使仓央嘉措如此虔诚,如此恪守职责,人们却依然对他的“情圣”身份更加关注,更多的人,更愿意寻找他偶尔散落在民间的“情歌诗集”。这究竟是佛的悲哀,还是世人的沦落?
或许,在人间,爱神,永远都比佛陀更加有魅力,爱情的力量,永远都比和尚的修行更加鼓动人心。你不得不承认,爱,是一种来自人心,最原始,最有威力的能量,无论在世俗的平原,或是在神圣的雪域高原。
不过,即使人们向往爱情,希望看到仓央嘉措描写的爱情诗歌,我也不得不为此解释一番。毕竟,“佛陀”和“爱情”,从来就只是被人们附会到了一起,远离那些美好的愿望,它们从来,就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仓央嘉措情歌”的原文题目是《仓央嘉措古鲁》。而在西藏,“古鲁”指的是“道歌”,而“杂鲁”指的才是“情歌”,后人以讹传讹,还是喜闻乐见地把这本诗歌集认为是情歌集。
然而,令人惊喜的是,我们依然在这本诗集中发现了某些与“情”有关的蛛丝马迹。
以曾缄先生翻译的仓央嘉措诗歌为例子,我们发现,仓央嘉措的确有一些诗歌,是以情歌的词句形式存在的。
曾缄先生曾译过仓央嘉措如下的一首诗:
入定修观法眼开,祈求三宝降灵台。
观中诸圣何曾见,不请情人却自来。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打坐的时候,佛祖的形象还没有出现在眼前,情人的身影却飘然而至,不请自来。
从字面意思看,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喜的词句,诗中的“情人”,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玛吉阿米?又或是传说中,仓央嘉措的数位情人之一?
然而,由于这首诗是用藏语写的,不同的翻译对诗的理解也有不同,我们无法仅凭一个翻译版本,就认定诗中的“情人”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我又找来了这首诗的另一个翻译版本:
我默想喇嘛的脸儿,心中却不能显现。
我不想爱人的脸儿,心中却清楚地看见。
由此来看,两位完全不同的翻译者,都将此诗翻译成情诗的模样。看来,这似乎确是一首情诗无疑了。
但是,我的心中却始终存在一个疑点。作为西藏地位最崇高的宗教领袖,仓央嘉措即使心有所属,又岂会将自己的心思明示在诗中,昭示天下。
此时此刻,他坐在尊贵无比的宝座上,即便可以用种种暗喻的方式,记叙自己无边的思念,又岂可用明喻的笔法,用思念,对抗佛法。
思念放在心中,或许还可以一直念想,放在嘴上,却可能连思念的机会都没有了。没有脑袋,什么机会都没了。
仓央嘉措,他真有这么大胆吗?
所以,要理解这首诗歌,了解仓央嘉措的宗教背景非常重要。
仓央嘉措修持的是密宗,在曾缄的译文中,有“观想”一说,而“观想”,其实是密宗的一种修持方法。这首诗歌其实是在说,仓央嘉措在“观想”之时,已能达到佛祖与己合二为一的境界,他说“情人不请自来”,其实是在用世人都了解的情人借喻佛祖,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观想境界。
事实上,后人将仓央嘉措的这首诗歌误认为是情诗,跟后人的翻译,也有着莫大的关系。曾缄先生是仓央嘉措诗歌的主要翻译者之一,他就极为喜欢在翻译这些诗歌时,加入自己的文采和意会。曾缄先生曾经翻译了这样一首仓央嘉措的诗:
静时修止动修观,历历情人挂眼前。
肯把此心移学道,即生成佛有何难。
不过,这样讲来,又一个疑点出现了。既然此处的“情人”即为佛祖,那翻译者,又为何不干脆以“佛祖”一词代入呢?我们可以来看看曾缄先生翻译的另外两首诗:
意外娉婷忽见知,结成鸳侣慰相思。
此身似历茫茫海,一颗骊珠乍得时。
为竖幡幢诵梵经,欲凭道力感娉婷。
琼筵果奉佳人召,知是前朝佛法灵。
从字面上来看,第一首诗的确是一首情诗。“娉婷”一词自然被理解为仓央嘉措的心上人。主要表达的是与意中人相爱的惊喜。他为自己能与心上人如此恩爱感到幸运和开心,把这种美好的感觉比喻为在大海里捞到了珍宝。
而在第二首诗里,“娉婷”一词显然出现了歧义,并且,它代指“佛祖”一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和汉语的表达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
在汉语中,表达“心上人”的词语不胜枚举,曾缄先生不必使用同一个词语既表达“心上人”又表达“佛祖”。并且,如果第二首中的“娉婷”指的是“心上人”就与“为竖幡幢诵梵经”矛盾。仓央嘉措只是一个迷失活佛,还不至于明目张胆到在公开作法的时候还想着心上人,并且直言不讳地说“我为了能感受心上人而大设讲经之坛”。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猜测,这前后两首诗中的“娉婷”,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即为“佛祖”。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解读那些被“错译”了的“仓央嘉措情诗”,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的诗歌中其实蕴含着许多宗教的含义。这不禁令人大失所望。
一旦我们还原仓央嘉措真实的历史形象,去除传说赋予他的各种形象,我们甚至可以颠覆对他诗歌的传统理解。或许,他留给人们“花和尚”的印象太深刻,使得翻译者对仓央嘉措有了先入为主的“多情和尚”的印象,从而使得翻译版本都向情诗靠拢了。
不过,这毕竟是一个令人惋惜的真相。对于爱戴仓央嘉措的人们来说,他们宁愿相信,他是布达拉宫里最为桀骜不驯的“情诗王子”,也不愿将那些美丽的诗词,跟枯燥无味的经文联系起来。
在层层残酷的剥离之下,“多情活佛”的故事化为了子虚乌有的云烟,多情缠绵的情歌全部成了礼佛之诗,有关“情种”达赖的幻想,随着高原的冷风,消失在了喜马拉雅的云端。
<!--mainContent end--><!--mainContent end--><!--mainConten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