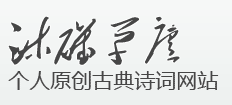林德涛 写于 2014年05月09日 06:13:21 浏览次数:1156 古人论诗选辑 作者林德涛
一、诗言志
“诗言志,歌永言”。志:意;言志,就是表达思想感情。歌:歌曲。永:通咏。永言:谓咏唱诗的语言。《尚书·舜典》。“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礼记·乐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载孔子语
二、诗无达诂
“诗无达诂”。达:通达;诂gu:训诂,解释。诗,很难用通俗的语言作出透彻而完整的解释,且不同的读者对其意境的理解和体味也不尽相同。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
三、诗与文,诗与词之不同
“诗与文体不类:文尚典实,诗贵清空;诗主风神,文先理道”。明·胡应麟《诗薮》外篇。“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清·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宜蕴籍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清·李渔《闲情偶记·词采》
四、诗与诗人的品德、襟怀
“诗品出人品”。清·刘熙载《艺概·诗概》。“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颂:同诵,吟咏。其人:他的为人。其世:所处的时代。春秋·孟子《万章下》
“诗之基,其人之胸襟也”;“志高则言洁,志大则辞宏,志远则旨永。如是者,其诗必传,正不必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志:立志。洁:简洁明净。辞宏:文辞雄健。旨永:思想深邃。清·叶燮《原诗》。“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襟抱:抱负。斯有:这样才有。清·沈德潜《说诗睟语》
五、作诗的四法
“律诗要法:起、承、转、合”。元·范悙《诗法》。“作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舂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舂容即宏大畅达;渊永即意味深长隽永。元·杨载《诗法家数》
六、诗不可无为而作,诗要紧扣主题
“诗不可无为而作,试看古人好诗,岂有无为而作者?无为而作者,必不是好诗”。清·薛雪《一瓢诗话》。“诗不着题,如隔靴搔痒”。宋·阮阅《诗话总龟》。“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意喻写景作品,不够真切。也用以比喻对事物看不清晰。清·王国维《人间词话》
七、诗是心声
“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清·叶燮《原诗》外篇上。“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清·李渔《闲情偶寄·戒讽刺》。“心之精微,发而为文,文之神妙,啄而为诗”。唐·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记》
八、诗萌生于灵感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这两句是对诗人李白身世的感慨。唐·杜甫《不见》。“作诗火急追亡逋,情景一失后难摹”。亡逋bu:逃亡者。比喻即将失去的诗意。宋·苏轼《腊日游孤山访惠勒惠思二僧》。
“有时忽得惊人句,费尽心机做不成”。宋·戴复古《论诗十绝》
九、诗要运用恰当的比喻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即广博比喻。安诗,写诗。《礼记·学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宋·朱熹《诗集传》
十、构思与磨砺
“启行之词,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启行:文章开头。逆萌:事先考虑。绝笔:终篇,结束。追媵ying:承接。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精:神。鹜:驰。八极:喻极远之处。万仞:喻极高之处。意谓诗人进行艺术构思,不受时空之限制而驰骋无边。晋·陆机《文赋》
“岂知儒者心偏苦,吟向秋风白发生”。唐·雍陶《少年行》。“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引唐·李频句。“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心源:构思的源泉。唐·贾岛《戏赠友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唐·贾岛《题诗后》
十一、改诗
“改章难于造篇,易字难于代句”。章:段。造:创作。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附会》。“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浮:不扎实。机:心机。窒:不通畅。清·袁牧《随园诗话》
十二、诗要继承和创新
“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会古人”。清·叶燮《原诗》外篇下。“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变:革新,通:继承。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
“诗要避俗,更要避熟”。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率意:随自己心意进行创作;造语:用词造句。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三》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背:违反。宋·吕本中《夏均父集序》
第二部分
一、“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 清·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写诗与做人是一体的,为诗做人,不可偏求一端。若不表现人,则其诗必然空而无味。“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清·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社会时代是诗反映的外在景象;人的主观情感是诗表现的内在灵魂。
二、“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清·王夫之《姜斋诗话》。无“意”之作,必定神情涣散,杂乱无章。“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浓而近者易识,淡而远者难知。”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文意重在深远淡雅。
三、“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已,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清·王国维《人间词话》。既能表达作者的深刻体会,抒发自己的感情;又能考虑读者的审美情操而感动读者,这才是写作的高层境界。
四、“眼不高,不能越众;气不充,不能作势;胆不大,不能驰骋;心不死,不能入木。”清·黄子云《野鸿诗的》。见识、气魄、胆量、心志,正是文章的灵魂。鹰击长空,方知天地之大;气贯长虹,始觉语能惊人;心存匡扶天下之志,才能驰思无限;专心致志,反复雕琢,才能大处着眼,小处着笔,刻划说理入木三分。
五、“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清·王夫之《姜斋诗话》。诗文之事,常常缘于景,动于景,融于景,然后让读者在欣赏景物的美好之时受到感动和启发,因景而情,因情悟景,情景不分,这时才会出现好诗好文。
六、“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将与风云而并驱也。”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七、“游寸心于千古,收八埏于一掬。”埏(yan),边远之地;掬(ju)用手捧土。明·袁黄《诗赋》。杰出的诗赋能以博古通今,融汇千古文萃集于寸心;以志高怀远,囊括八方远土捧于一掬。
八、“善言情者,吞吐深浅,欲露还藏。”明·陆时雍《诗镜总论》。大凡文章最难在于适度,言过多过直则显浅薄,言过少过虚则未达意。犹如画山水之藏笔,不见收笔,则交代不清,净见收笔,则十分浅陋。神奇与美妙,全在含蓄之中。所以,在抒情诗文中,描写适度、含蓄深邃,才是最耐人寻味的。
九、“八句诗,何以名律也?一为法律之律,有一定之法,不可不遵也;一为律吕之律,有一定之音,不可不合也。” 清·徐增《而庵说唐诗》。“綦组锦绣,相鲜以为色;宫商角徽,互合以成色。” 明·胡应麟《诗薮》。律诗是一种平衡对称、参差整齐、结构严谨,其音、形、义相互谐调又富于变化的具有格律规则的诗体。
十、“词之为题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清·王国维《人间词话》。词柔丽睿永,含思婉转,宜于抒发人心最细微的感情,能创造难以言传的意境。所以说,诗重于言志,词重于抒情。
十一、“今天下非无诗也,无选诗之人;非无选诗之人,而无知诗之人,非无知诗之人,而无平心论诗之人。”徐增《贻古堂诗序》。徐增是明末清初一位有见识的诗论家。
十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清·王国维《人间词话》。这是以晏殊《蝶恋花·怀人远念》、柳永《凤栖梧·竚倚危楼风细细》和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名句喻人生之三境界,是在事业上和学问上取得重要成就所须经历的三境界,也是写好诗必须的三境界。
第三部分
一、“词赋文章能者稀,难中难者莫过诗”唐·杜荀鹤《读诸家诗》。
二、“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唐·韩愈《进学解》。
三、“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宋·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四、“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拘:扣押。厄:被困。厥:乃。吕览:《吕氏春秋》。《诗》:诗经。
五、“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唐·韩愈《县斋读书》。共赋:一起吟诵。孤斟:独饮。
六、“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 唐·韩愈《答张十一》。斗,通“陡”,突然。
七、“昔有以诗投东坡者,朗诵之,而请曰:此诗有分数否?坡曰:十分。其人大喜。坡徐曰:三分诗七分读耳。”宋·周密《齐东野语》。原意是:诗作不佳,要靠朗诵取胜。现在讲“三分诗,七分读”则是用以说明诗本是为吟咏的,作品需要诵读来用心体味,读之不顺,诗必有瑕;读之朗朗,诗必煌煌;相反,如不认真诵读,好诗也品不出诗味来。
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被文以入情。”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缀文者:作者;观文者:读者;被文:分析文章。
九、“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操:掌握;晓声:通晓声律;识器:掌握评价物品的要领;圆照之象:全面观察分析体悟作品的优劣;务:一定,务必;博观:开拓眼界,广博观察。学诗也是如此,应广博阅读,细心体味,谓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十、“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宋·王安石《上人书》。意为写文章一定要对社会有实用价值,诗也应如此。
十一、“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清·赵翼《论诗五绝》。钧:制陶器用的转轮。前两句意为:天工化育为万物,如陶匠的转钧,客观事物生生不息,日新月异,诗人的创作也如天工造化那样争相显示新意。后两句又以数字概念让人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必然。
十二、“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赵翼《论诗五绝》。领风骚:诗坛之首。风骚:《诗经》中的《国风》和《楚辞》中《离骚》合称为风骚。
第四部分
一、“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精神亦无喻矣。”清·刘熙载《艺概》。诗人的真实情感必须通过气象、形象、比兴来表现其精神意境的。
二、“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合。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归真也”《庄子·渔父》。诗人无论托物喻志,借景抒情都应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万不可矫揉做作,假情假意。
三、“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言类,以形之有情欲书、天机随触,每接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复唱叹,而中藏之欢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清·沈德潜《说诗睟语》。说诗人须把自己思想情感联系同类事物的形象来表达,比兴是写诗的重要方法。
四、“咏物以托物寄兴为上,一经刻画,逐落蹊径。” 清·薛雪《一瓢诗话》。
五、“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儿童猜谜。” 清·袁枚《随园诗话》。
六、“人的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 清·吴乔《围炉诗话》。
七、“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谢榛《四溟诗话》。
八、“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知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却然有如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宁独在诗文一道已也。”清·叶燮《原诗》
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无邪。”《论语·为政》载孔子语。《诗》三百:《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蔽之:概括。思无邪:思 指思想,无邪指不邪恶。
十、“学诗须有才思、有学力,尤要有志气,方能卓然自立,与古人抗衡。” 清·薛雪《一瓢诗话》。
十一、“必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后为我之诗。”清·叶燮《原诗》。
十二、“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隐秀》。英蕤(rui):精华。隐:含蓄。秀:特别突出的句子。文外之重旨:文辞之外另一层深意,通过文辞明说的是一层意思,所要暗示的又是一层意思,故称“重旨”。独拔:突出挺拔的文句。
第五部分
一、“倚马休夸速藻佳,相如终竟压邹枚。物须见少方为贵,诗到能时转是才。清角声高非易奏,优昙花好不轻开。须知极乐神仙境,修炼多从苦处来。” 清·袁枚《箴作诗者》。速藻:指宋·沈璞所作《旧宫赋》不如此前之作敏捷的事,意不要夸奖快速写作。邹:邹阳,才思敏捷;枚:枚皋:作赋快手。相如:司马相如,虽写作较慢,作品数不及枚皋多,但其成就终在二人之上。转是才:能反复推敲者才是真正有才华的人。角:宫商角徵(zhi)羽,五音之一,声调高,奏之不易。颈联,意为好诗不易得到;尾联,正因如此,故需修炼。
二、“作诗能速不能迟,亦是才人一病。心余《贺熊涤斋重赴琼林》云:‘昔着宫袍夸美秀,今披鹤氅见精神。’余曰:‘熊公美秀时,君未生何由知之?赴琼林不披鹤氅也。’心余叹曰:‘我明知率笔,然不能再构思。先生何不作诗以示我?’余唯唯。迟半月,成七绝句,心余以为佳。余乃出簏中废纸示之曰:‘已易七稿矣’心余叹曰:‘吾今日方知先生吟诗刻苦如是,果然第七回稿胜五六次之稿也。’余因有句云:‘事从知悔方徵学,诗到能时转是才’。”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心余:清朝诗人蒋士铨,字心余。余、余曰:袁枚,袁枚以其和蒋士铨一段创作经历,来论证作诗不宜过快的问题。袁枚所重之“迟”并非天生迟钝,而是有才而不炫才,精益求精。当然袁枚也很辩证指出有时“天机一到,断不可改”“知一重非,进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铸而定”。
三、“论定诗人两首诗,簪花人作大宗师。至今头白衡文者,若个聪明似女儿。” 清·袁枚《上官婉儿》。唐才女上官婉儿,受中宗命,殿前登彩楼,评骘臣僚百余篇诗作。落选诗皆落下,仅余沈佺期、宋之问两篇。婉儿沉思良久,沈诗飘落,宋诗夺魁。婉儿评价:沈宋两诗工力相近,只是结尾上,宋诗为优。沈以“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结篇,两句为谦语,且出题外;宋以“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紧扣晦日的无月时令;又用相传昆明池神鱼献夜明珠的典故,切合地望,显现帝王豪华景象,且辞意不尽,故而为上乘。袁诗正面赞颂了婉儿这一段佳话,又隐约讥讽与袁同时代的保守诗论家沈德潜。沈主张以格调论诗,以时代限诗(尊唐抑宋)等迂腐保守观点。袁主张写诗要抒灵性、无宗无不宗,强调独创、有识,“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随园诗话》。
第六部分
一、“诗有力量,犹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时,不知其难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处,分寸不可强。”宋·许凯《彦周诗话》。
二、“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故曰: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 宋·严羽《沧浪诗话》
三、“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宋·姜夔《白石诗说》。气象:指诗的体态风貌,外在表现和气质气度。气象有大小、宽狭、厚薄、强弱之区分。浑厚:即浑然天成,拙朴率真,自然通透之意。俗:庸俗。体面:指诗的风格与个性。宏大:博大精深、绚烂、壮丽。狂:狂怪,过于随意,不符合艺术规范,迎合世俗趣味。血脉:指诗的脉络。贯穿:贯通。露:露怯,不谐调。韵度:指风韵、神韵、气韵。轻:轻浮。
四、“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一曰意高妙,一曰想高妙,一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宋·姜夔《白石诗说》。
五、“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志之所之:诗乃由志而产生。“情动于中”以下五句:指心中有情感而后用语言传达出来;意犹未尽,则继之以咨嗟叹息;再有不足,则继之引声长歌,且手舞足蹈。
六、“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声成文谓之音:声,指宫、商、角、徵、羽;文,由五声和合而成的曲调;将五声合成为调,即为“音”。 乖:反常。莫近于诗:莫过于诗。经:常道,用作动词,意为使归于正道。
七、“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毛诗序》
八、“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周礼·春官·大师》
风:指《诗经》中的国风。赋:指《诗经》的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比:比喻手法。兴:起的意思,指具有发端作用的手法,这种发端有时兼有比喻的作用,有时只为音律上的需要,而无关乎意义。雅:指雅诗。有正的意义,谈王政之兴废。大小雅的配乐,时称正声。颂:指颂诗。有形容之意,即借着舞蹈表现诗歌的情态。
九、“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清·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以境界说作为评判古来词作的主线。
十、“立身无傲骨者,笔下必无飞才;胸中具素心者,舌端斯有惊语。”明·沈承《晚明小品文库· 沈君烈传》。君子为人,当刚强时壁立千仞,无俗而刚;当清淡时,放浪形骸,驰骛八极。只有这样,才有飘逸的神采,惊人的词语啊。
十一、“推天地于一物,横四海于寸心。”南朝宋·谢灵运《入道至人赋》。好文章以小见大,以我心见天下。则文章的内涵丰富,而气势恢弘。
十二、“古人文章似不经意,而未落笔之先必经营惨澹。”清·吴行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好的文章写起来一气呵成,似乎不经意,不用心,随心所欲;而在文章下笔之前,则苦心经营烂熟于胸,必然久矣。说提笔可得,而胸中早有文章;说经营久远,而付诸笔端时一泻千里,这才是作者千锤百炼的深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