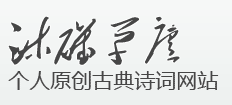大洲 写于 2002年08月10日 08:33:16 浏览次数: 8787 沐矶和他的诗词
沐矶和他的诗词 大 洲 1998年晚秋的一天,我去市人民保险公司,与公司经理沐矶商谈举办人民保险杯好书伴我行读书征文活动的事宜。那天巧的是,副刊上登了他的一首小诗。于是谈完正事,就抒闲情。 实话实说,那首题为《送友人》的诗,如果不说是他写的,我并不看好。浅白如话,格调不高,无甚新意,不过一顺口溜而已。但这诗最终能引起我的兴趣,并且还为此说了一些好话的原因在于,身在商场官场中的他,竟有此闲情逸趣?或者说,在他的心灵深处,还葆有着那么一片难得的文学净土和难得的向善向美向真之情,实属难能可贵。我还记得,当时的副总编给他改了最末的一句,他竟为此耿耿于怀,大为不满。这种执着认真的精神更令我对他刮目相看。这不是固执或者自恋,言辞间争执的是对诗艺的追求。 于是我对他说,你这诗虽然短小,虽然词白意浅,但也清新宜人,虽是白描,但写人如画,情态毕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作者对普通人的尊重与关怀。看得出,文字功底很好,有才情,有诗心,常写写,会写得更好。 没想到,我的话令他大为感动,感动得他从写字台最下方的抽屉里,拿出了据说是从不示人的笔记本来,让我看看他的其他作品,确切的说,是他填的词,三首《江诚子》! 当然,他对我的信任,倒不仅仅是因为我的这一番“花言巧语”,以及因此而与他迅速拉进了感情距离。其实在这之前就与他相当熟了。都是在小城市里长大的,父母一辈都有来往,我虽长他四岁,但我的三弟与他要好,我也就跟着认识了。他那时人长得水灵灵的,号称“金童”,而且很喜欢文学,我在上中学时就对他有很深的印像,但“亲密接触”,却没有机会。但现在,他自己敞开了心灵之窗,邀我步入他的精神世界,并且从此,成为挚友。 说实话,我在读他的词时,意识之流却流向了许多年前学词时的大学课堂。那时教授说填词算得上绝学了,现代人填的好的了了无几,大多是附庸风雅,有形无神。格律诗词,已被古人写尽写绝,后人唯有欣赏的份儿。他甚至自我解嘲,说他谈词头头是道,却一首像样的词也填不出,这就是词为绝学的最好例证。我那时学到词的格律时,平平仄仄,京冬大韵,仿佛天书一般,根本就不朝脑子里进,自然对填词视为畏途,对敢于填词的人,要么十分轻蔑:他竟敢填!要么十分敬畏:他竟能填!而眼前的这一位本就与吟诗填词的风雅之事八竿子沾不到边的沐矶竟也敢填甚至能填词,而且这还是个刚发表了一首顺口溜式的所谓七律的家伙。 但我此时之所以会很认真地读他的词,因为一者我自己不懂词律,不敢妄下褒贬断语,二者沐矶显然很看重他的词作,对科班出身的我十分信任;三者这些言情词里,的确非抄袭非无病呻吟,内里有着令人不能不怦然心动的深挚而又复杂的情愫。 还记得先品评的是《江城子.曾经牵手》。那是一首怀人忆旧伤情之作。我不知这首词写的是不是沐矶自己的所历所感所思,当时也没问他,因为这类题材在旧体诗词里,算得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可以写自己刻骨铭心的情感,可以为别人依声填词抒情言爱,或者唱和吟咏;可以直写情爱,也可以借对爱情的咏叹,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甚至于政治的抱负。也正因为如此,词才成为艳科,词才得到人们广泛的共鸣,人们从爱情的咏叹中,各取所需,享受着独异的精神美餐。 词的上片是忆旧,回忆曾几何时与旧友最难忘的也是最后一次的春游。那是盛春时节,“草长莺飞”大自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一切都欣欣向荣,然后词人的这一段感情却已到了穷途末路,更确切的说,是因为现实的某种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里,来结束这一段情感。正是以乐景写哀景,一倍增其哀。 “牵手踏青游”,最后的别离竟开始于美好的结伴而游,可能此时词人(这里的词人只是抒情主人公,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还不知道最后时刻的到来,所以她在自己的眼里,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美丽迷人:“低回眸,俏含羞”。词人不写其肖像,不写其声音,不写其体态,只写其眼神,却将其娇美情态如画般活脱脱跃然纸上,突显于读者的面前了:低垂着眼帘,时不时地偷看上词人一眼,因为她的“含羞”而益发显得俊俏,令人着迷。想来那时的词人已是眼迷神醉了吧?这写法含蓄蕴藉,深得传统诗词写人之三味。 踏青而游的过程一带而过,读者可以依据自己的经历给以合情合理的想像,词人所特意推出的只是一个特写的镜头:“岸柳系归舟”,这与其说是写景,不如说是写人,更不如说是写心写情,也因此,成为上片中最造情境的好句。 春游结束了,在岸柳上系上小舟,而一段情感也就此了结!岸柳虽然能系得住小舟,可系不住人心,系不住感情。岸柳的柳丝儿再长,也栓不住情人离去的心。“归”字暗喻了情人离去之心的决绝,一段感情就此永远定格在了这岸柳小舟的情景之中。 于是满腔的痛楚若破堤之水,汹涌奔腾而出:“世上诸余难耐事,人别后,泪双流。”词人的绝望痛苦之情无以言喻:世上再多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事,都不如与情人分离更痛苦。男儿有泪不轻掸,而此时,词人忍不住热泪双流,而且是毫无顾忌,由此可见情伤之深之重了。其实人世间又岂止是爱情之伤呢?友情亲情之伤,也复如此呢!所以这三句我也吟诵再三,自己也不禁有些眼潮了。 下片是写离别多年后的苦思苦恋之情,是直抒胸臆。“韶华已逝”也不过是人到中年,可是却已是“尘霜头”了。这一句是写实,那时的沐矶年龄不到四十,头发却白了许多,又不愿染发,于是剃了个小平头。上级领导有些看不惯,以为作为公司一把手,这样太不庄重。这批评让沐矶很是伤心,却又不多解释,但依然故我,留着他的小平头直到今天。我曾想他的仕途不顺,可能与这小平头多少有些关系。实际上,他的过早发白,根本原因,还是与他事业有关。他不到三十岁时,就当了公司副经理,是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后来公司一分为二,他三十出头,就做了公司的一把手。那时公司亏损严重,业务开展步履维艰。上任后的沐矶,每天五六点起床上班,从不休星期天,几年如一日,惮精竭虑,卧薪尝胆,终于有了今天事业的辉煌。在苏北的县级公司中,他的公司业绩最好。而为了斐然的业绩付出的那许许多多中,就有这“尘霜头”吧?当然对于不了解他的经历的人,在词里是读不出这些故事来的,也是不可能知道他的词,还有着其他寄托的。其实以写恋情,寄托人生感慨,寄托人生理想,也是惯用传统手法。当然沐矶词也可能二者皆有吧? 说“念思悠”好解,情多深,思念就会有多长,但说“恨难休”,似乎就有着许多不可知的隐情在其中。因爱生恨?所恨何人?为何而恨?是恨自己的过失?还是恨恋人的绝情?……词人不说透,读者只好乱猜,总而言,各以自己的生活阅历,来想像那可能发生的情节吧:什么样的恨,如此难以化解呢?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思之甚切,梦之愈真。而词人所能聊以慰藉相思之苦的也只有“梦里惟求,重续旧温柔”了。梦虽然代替不了现实,但退而求其次,“纵使梦魂同是虚,能忘却,许多愁”,这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一种无奈的超脱。而一个人只有在梦里才能忘却许多愁时,也足可见其愁是何等的沉重了——那是每天每时缠绕于心的愁思呢! 虽然这词不脱旧体诗词抒写儿女情长的套路,用词也浅白,但今人能写到如此地步,也是不易,更何况写得情真意切,词句也委婉流转,合辙押韵,读来上口,又能打动人心,且情景交融,实属难能可贵吧?不过那个“念思悠”总不如“思念悠”来得顺畅,说是为合平仄而不得不硬性颠倒词序,但总觉别扭。而第二首《江城子》最后一字也用个愁”字,似乎也嫌重复。三作中两次出现“泪双流”、“双眼泪”似乎少了变化。还有,“青袖泪”显然从“青衫湿”化用而来,但后者代指官职,其实代指的是诗人自己,而此处的“青袖”又该当何解”,似乎也无着落。……当然,这些都是见仁见智的看法,未必恰当,好坏说完了,我就说些坏话,反正是知已朋友,不会以此伤了和气。而诗词写作,历来都是要切磋世磨,沐矶虚心一一听来,我也就直言不讳了。 综观这三首《江城子》,是自成系列的。第一首写最后分别,第二首写旧地重游,第三首直抒胸臆。不过令人纳罕的是,这三首词写作的时间跨度,竟是三年,一年只写了一首!我问为何如此难产,沐矶笑而未答。 与第一首《江城子》比较,第二首词则更显哀婉凄切。无论是古桃叶渡,还是庭院空楼,总是物依旧,人已非,悲苦痴情的词人或“痴望断,远帆舟”,其实那远帆之舟上又哪里会是远离的人呢?或是“醉眼扶墙”听“邻里哀筝”,误把墙作人,筝声岂有哀,总是内心苦楚至极而生幻觉罢了。 第三首词,感情基调似乎是悲愤了:“两情何故尽轻抛”?是的,为什么会毫不留情地彻底地抛却旧情,而且还是轻易地就抛弃了呢?人间果然真情难觅?悲愤之后是绝望,于是“惟有恨”时,便“转无聊”,这时的内心似乎已麻木了。下片写词人独上寒桥,顶风而立,看“水吞礁,小船摇”,强把无限悲凉凄苦压于心里,正是欲说还休,“风里任随飘”。这首词是为抒情主人公造像,若浮雕,过目难忘,此地无声胜有声。 就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会儿火一会儿水的,与其说是在与沐矶品词,不如说是在品人生,品心灵,品生命,品情感。若说他的词艺术上有如何造诣,那不客观,是溢美。但学词初步,能浅入堂奥,并得其真味一二,也实属不易,足已令人刮目相看了。要知道他业务极繁忙,应酬甚繁多,俗务缠身,花红酒绿,又哪里会有时间和心情填词呢?这对我来说,倒算是个谜了。 其实沐矶还是具有很深的文学素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