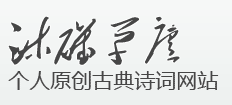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
浏览次数:12511 李玲 写于 2009年12月18日 01:41:01《长恨歌》在书写“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时,把既日常又时尚的上海风情铺写得入肌入里。这体现了作家把握地域文化特征、洞悉世态人情方面的卓越才情,但令人遗憾的是,隐含作者在营构女性人物关系时,认同了以情色等级、世俗精明程度评定女性生命价值的世俗观念;在设置男女人物关系时,欣赏的是女人自愿为女奴的乖巧、势利;在品鉴日常生活情味时,表露出的是对女性身上的奴性只有体恤没有反思的态度。这样,《长恨歌》文本就确定了它认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完成了它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
一
《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的故事分别在她与众女性、与众男性的关系中展开。在王琦瑶与众多女性人物的关系设置中,隐含作者在价值立场上纵容了以色相等级来区分女性生命价值、以世俗精明来睥睨生命真诚的世俗价值观念。
王琦瑶学生时代的女友有吴佩珍和蒋丽莉两个。这两个女同学的共同特点一是长得丑,二是单方面忠诚于王琦瑶,三是不如王琦瑶精明。“吴佩珍是那类粗心的女孩子。她本应当为自己的丑自卑的,但因为家境不错,有人疼爱,养成了豁朗单纯的个性,使这自卑变成了谦虚,这谦虚里是很有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的。……王琦瑶无须提防她有妒忌之心,也无须对她有妒忌之心,相反,她还对她怀有一些同情,因为她的丑。……王琦瑶的宽待她是心领的,于是加倍地要待她好,报恩似的。”
按照世俗观念说吴佩珍“本应当为自己的丑自卑的”,全知第三人称叙述者居高临下的语气相当冷静。这种冷静,使得这个句子的叙述态度显得复杂难辨。它表明叙述者可能是认可世俗观念而冷眼对待丑人,也可能是不动声色地讽刺了丑就应当自卑的世俗观念。这两重相抵牾的意味并存,叙述者在一定程度上既与丑人“应当”自卑这一世俗观念保持了距离,也与被这个观念所伤害的丑人保持了距离。接下来说吴佩珍“因为家境不错,有人疼爱,养成了豁朗单纯的个性”,是对丑人个性的肯定,仿佛超越了以美丑判断生命等级的世俗观念,但这句话其实不过是欲抑先扬,为下半句对丑人的贬抑做准备。下半句“这谦虚里是很有一些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判断中,隐含作者的立场完全倒向世俗价值立场,抹去了与世俗价值观念之间的距离,完全被“丑就应该谦虚”这一庸俗观念牵着鼻子走。以“实事求是”的陈述认可以美丑决定生命等级的世俗观念,那一点冷静中透出的漠然态度就单向度地刺向了丑人,不再在丑人与庸俗生命观念之间走钢丝追求平衡了。这第二个句子,尽管百转千回,事实陈述层次和价值判断层次的内涵都很丰富,充分显出了隐含作者体察人性的功力,也显示了隐含作者价值立场的多重性,但是隐含作者的核心价值立场还是认可了以美丑划分女性生命价值的庸俗观念。
“王琦瑶无须提防她有妒忌之心,也无须对她有妒忌之心,相反,她还对她怀有一些同情,因为她的丑”,显然不是人物独白,而是“即述即议”(1),是叙述者对人物关系的陈述、判断,同时也包含着叙述者对人物王琦瑶心理的揣摩。叙述者的这一陈述、判断,是以女孩只要长得丑就没有什么值得自傲这一观念为立论前提的。显然,叙述者、隐含作者在对世俗观念放弃审视、批判而采取单一的理解态度时,就已经放弃了客观、中立的价值立场了,所以最终不免完全确认了这样的世俗逻辑:美女与丑女交朋友的心理基础是“同情”,性质是“宽待”;丑女对美女好则是“报恩”。
在文本后面的叙述中,吴佩珍想方设法讨王琦瑶的欢心,一直处在报恩的被动位置上;王琦瑶动辄给吴佩珍脸色看,一直按照自己的心绪决定着要不要接受吴佩珍的友情。而隐含作者、叙述者对美女的这种特权没有任何质疑,只是在貌似“零度”的叙述中予以全盘理解。这样,隐含作家便进一步确立了其评价女性生命价值的首要尺度是色相美。隐含作者终归默认了这样的世俗观念,即漂亮与否决定了女人尤其是未嫁女人的生命等级。
默认以色相美丑界定女性生命价值这种世俗观念的叙述态度,贯穿全书。它还体现在作家对王琦瑶与女儿薇薇的对比评价中、体现在张永红与薇薇的对比评价中。把色相美丑这种自然属性作为绝对尺度来界定女性生命等级,实际上就把女性的主体意识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放逐了女性作为超越生物性存在的人的精神价值。(2)
凭着美色优势,王琦瑶不必把心掏出来与朋友相处;吴佩珍、蒋丽莉没有色相美,只能把心掏出来奉献给王琦瑶。她们除了心之外,还奉献出社会关系、家庭实力为王琦瑶挤进繁华世界服务。吴佩珍把王琦瑶引进电影片场,使得王琦瑶获得了一次试镜机会,但王琦瑶终因自己不擅长表演而未成影星,这样吴佩珍就由于目睹了王琦瑶的失败而失去了王琦瑶施舍的友谊。蒋丽莉因为帮助王琦瑶选美成功,而终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系住了王琦瑶施舍的友谊。但在隐含作者的叙事立场中,王琦瑶由冷酷和自恋所产生的种种小心眼,都成了女性的聪敏,叙述者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投之以温情的体贴、怜惜。而吴佩珍、蒋丽莉对朋友的热忱却成了缺心眼、傻冒,叙述者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投之以略带轻蔑的揶揄。
吴佩珍通过表哥的关系安排好带王琦瑶去电影片厂玩,“不料王琦瑶却还有些勉强,说她这一天正好有事,只能向她表哥抱歉了。吴佩珍于是就一个劲儿地向王琦瑶介绍片厂的有趣,将表哥平日里吹嘘的那些事迹都搬过来,再加上自己的想象。事情一时上有些弄反了,去片厂倒是为了照顾吴佩珍似的。等王琦瑶最终拗不过她,答应换个日子再去的时候,吴佩珍便像又受了一次恩,欢天喜地去找表哥改日子。其实这一天王琦瑶并非有事,也并非对片厂没兴趣,这只是她做人的方式,越是有吸引的事就越要保持矜持的态度,是自我保护的意思,还是欲擒故纵的意思?反正不会是没道理。吴佩珍要学会这些,还早着呢。去找表哥的路上,她满心里都是对王琦瑶的感激,觉得她是太给自己面子了。”
王琦瑶如此拿捏造作,不过是要让自己在事情和人面前都占强势地位,至于说待人诚恳,那是不在她的自我要求之中的。然而,权威叙述者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中,还是把一点温情投注给了王琦瑶,把一点嘲讽投注给了吴佩珍。王琦瑶的“矜持”到底“是自我保护的意思,还是欲擒故纵的意思?反正不会是没道理”这一揣测中,叙述者的语气显然是怜惜、理解王琦瑶的。可见,叙述者、隐含作者都愿意悉心理解王琦瑶操纵局面、拿捏朋友的小聪明,并不愿批评她没有真心待朋友的缺点。“吴佩珍要学会这些,还早着呢。去找表哥的路上,她满心里都是对王琦瑶的感激,觉得她是太给自己面子了”,这句话紧接在对王琦瑶的怜惜之后,联系上下文,应该可以排除作者为吴佩珍鸣不平的意味。显然,权威叙述者、隐含作者在貌似冷静中还是暗暗认同了把吴佩珍的真诚界定为不成熟、低智商的世俗观念,从而进一步确认了王琦瑶小聪明中 “高处不胜寒”的“境界”。这样,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评价上,《长恨歌》在色相等级这一评价尺度外,又添加了世俗精明这一评价尺度。由于小说在人物设置上,总是让女性的色相等级与精明等级成正比,这样,世俗精明这一尺度不仅没有瓦解色相等级尺度,反而对它起了加固作用。
在王琦瑶和蒋丽莉的关系中,王琦瑶原本看不上蒋丽莉这种长得不美、又带着文艺腔的同学,但因为考虑到蒋丽莉上流社会这一家庭背景,王琦瑶才决定接受蒋丽莉的邀请。
“她(指蒋丽莉)功课一般,却喜欢在课间看小说,终把眼睛看成了近视,戴着洋瓶底厚的眼镜,那样子越发不可接近。”
“她(指王琦瑶)不喜欢这种文艺腔的把戏,那些写在纸上的字句总有点叫她肉麻。”
“第二天,王琦瑶又在书本里看见一页信笺,淡蓝色,角上印花的那种,写着诗句般的文字,歌颂的是昨晚的月亮。王琦瑶不免心里有些起腻。”面对蒋丽莉因友情而流的泪,王琦瑶“心里倒有点好笑,也有点嫌烦,还有一点感动,是不得已,被逼出来似的感动。”
从王琦瑶这个“起腻“”、这个“有点嫌烦”的立场上看蒋丽莉,蒋丽莉少女时代充满激情的友谊,蒋丽莉对文艺的爱好就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之所以“起腻”、之所以“有点嫌烦”,是由于王琦瑶心中从来没有产生过和蒋丽莉共鸣的情感。这一是因为王琦瑶极度自恋,心中本就不容易滋生忘我的友情;二是因为她原本和蒋丽莉就是两个世界中的人。王琦瑶是现实世界中的人,一切都极为功利实际;而蒋丽莉则活在小说滋养的梦想世界中。然而,权威叙述者只是不断从王琦瑶这个“起腻”、“有点嫌烦”的立场上看蒋丽莉,却从没有站在蒋丽莉的“文艺性”立场上理解过蒋丽莉的激情、蒋丽莉的书卷味。这样,蒋丽莉的世界从来就没有获得和王琦瑶世界对话的权力。由于隐含作者、叙述者拒绝从蒋丽莉的视角看问题,蒋丽莉在小说中就一直没有获得表白心理逻辑的机会,这样,她和现实世界的不和谐,就只能按照王琦瑶的现实生存法则而被归咎于性格的别扭。至于她的文学爱好、她的激情,是否有其梦想飞翔、超越现实的合理性,就不被关注了。作家体恤的只是王琦瑶因为蒋丽莉过分热情而让王琦瑶产生的压迫感。
这就更加重了对蒋丽莉激情、文艺腔的否定、嘲讽。直至蒋丽莉病入膏肓、大限将至的时候,她那些抒写一生爱情之痛的诗句,虽然让王琦瑶深受感动,但王琦瑶的感动仍然只是认定蒋丽莉是矫情者前提下的感动,包含着判断上的不公平。权威叙述者站在王琦瑶的立场上议论说“它们再是矫情,也因着天真而流露出几分诚心。”然而,蒋丽莉一生陷在无望的爱情中饱受折磨,还怎么能说她是矫情的呢?判断蒋丽莉只是在矫情中还含着“几分诚心”,归根结底还是王琦瑶以及代表隐含作者立场的权威叙述者从根本上就认为刻骨铭心的爱就是矫情、写诗就是矫情。她们只相信现实生存层面上的患得患失,不相信激情。文中,尽管全知叙述者是以“混和着欣赏和挑剔的笔致”(3)来对待笔下人物,显出隐含作者思维的辩证性。但显然,在叙事部分,对待美人王琦瑶的态度是“欣赏”、怜惜压倒“挑剔”,走向了偏袒;对待文艺青年蒋丽莉则是“挑剔”、揶揄压倒了“欣赏”,流于刻薄。
整部小说中,叙述者、隐含作者对许多人的内心都有深切的探究和理解,哪怕像李主任这种包养情妇的阔人、像康明逊这种不能对自己的性爱负责的男人、像长脚这种谋财害命的杀人犯,叙述者、隐含作者都愿意去领会他们的生命逻辑。这体现出隐含作者探索人性的兴趣和理解人心的智慧深度。但独有对蒋丽莉,叙述者只是让她一味地别扭,别扭一生。这种简单化的否定处理,是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使然。隐含作者此时的价值观,是认同现实性原则,厌憎诗性原则,鄙视精神追求的。
尽管吴佩珍、蒋丽莉这两位丑女愿意无条件为王琦瑶服务,但王琦瑶倒也并不想占便宜。王琦瑶一住进蒋丽莉家,就立刻帮她们家整顿好主仆秩序。“王琦瑶住进蒋丽莉家,还是和蒋丽莉搞了平衡。她是还蒋丽莉的好,也是还她的权力控制。这样,她们就谁也不欠谁,谁也不凌驾于谁了。”王琦瑶还的是现实的人情,而不是在情感上对蒋丽莉的友情作出回应。这虽说明王琦瑶不是不知好坏、不讲善恶的无耻之徒,但也说明王琦瑶的心是冷的。她遵循现实的人情报答规则而放逐真淳的情感。充分体恤她、不忍批评她的叙述者、隐含作者,在这一点上也就不免降到了和她同一精神高度上了。
叙述者、隐含作者并没有让吴佩珍像蒋丽莉那样不得善终,而是让她最后一次亮相的形象定格为一个令王琦瑶羡慕的中产阶级太太。吴佩珍命运的设置中,暗暗透露出隐含作者“憨人有憨福”的宿命观念。这一隐隐的宿命观念,对贯穿全书的欣赏世俗精明的叙述立场构成补充。隐含作者、叙述者尽管认同吴佩珍的命运,但真正怜惜的还是王琦瑶那“心比比干多一窍”的世俗精明。
二
王琦瑶与男性世界的关系首先是她与李主任这位阔人的关系。王琦瑶和李主任的关系有三个特点:首先,这种关系的本质是男性权势与女性情色之间的交易;其次,王琦瑶在这种关系中是一个被动屈从、完全没有主体意识的女奴;再次,王琦瑶是自主选择女奴道路的。致命的问题是,隐含作者、叙述者是理解了而不是批判了这种男女关系。这样,《长恨歌》文本就确定了它认同女性女奴身份的文化立场,完成了它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化作用。
乖觉可人是“沪上淑媛”、“上海小姐”王琦瑶女性风情的核心,但这种乖顺只体现在王琦瑶的公众形象中、在她与李主任这位权势男性的关系中,而不在王琦瑶与吴佩珍、蒋丽莉这些色相不如她的女性的交往中,也不在她与程先生、导演这些没有显赫权势的男性的交往中。
“照片里的王琦瑶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乖。那乖似乎是可着人的心剪裁的,可着男人的心,也可着女人的心。她的五官是乖的,她的体态是乖的,她布旗袍上的花样也是最乖的那种,细细的,一小朵一小朵,要和你作朋友的。” 在公众视野中取得乖顺、贴心的美女印象,是王琦瑶引起李主任关注的前提条件。王琦瑶终不过是李主任所宠幸的众多女人中的一员。对于李主任而言,“……女人还是那么不重要,给人轻松的心情,与生死沉浮无关,是人生的风景。女人也是李主任的真爱,但爱不是李主任的人生大业,连附丽都谈不上的,有点奢侈的意味。但因李主任有实力,便也谈得上奢侈了。” “李主任的正房妻子在老家,……另有两房妻室,一房在北平,一房在上海。而与其厮混过的女人就不计其数了。”之所以心甘情愿作李主任的外室之一,“王琦瑶也不是爱他,李主任本不是接受人的爱,他接受人的命运。他将人的命运拿过去,—一给予不同的负责。王琦瑶要的就是这个负责。”显然,与李主任的关系中,王琦瑶是不谈爱情、不谈平等的。她谈的是“恩”和“义”。这“恩”“义”就是李主任充分保障了她生存的物质条件。她的相思、苦等,她单方面的忠贞不二,便是对这所谓“恩”“义”的回报。
显然,王琦瑶是“一个依附与依赖男人,靠出卖色相来换取荣华富贵的依人小鸟”(4)。而且,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她又是恪守“女奴”道德的,决不把自己作为平等交易的主体去审视李主任的世界、去和李主任讨价还价,因为“李主任是权力的象征,是不由分说,说一不二的意志,唯有服从和听命。”王琦瑶凭着本能就明白把女性的主体性压得越低、把女人的奴性发挥得越极致,就越有可能获得男性主人更多的宠爱。所以,苦等李主任的时候,她连赌气也不敢。“赌气这种小孩子家家的事,怎么能拿来去对李主任呢?和李主任赌气,输的一定是自己。”在爱丽丝公寓的日子里,“王琦瑶从不追问李主任从哪来,又到哪去,政局和公务是她不懂也没兴趣的。李主任的私事,她又不便过问,过问也是没趣。”在朋友圈中自尊敏感、精明厉害的王琦瑶,在李主任显赫的权势、充足的金钱面前,变成了一个乖顺被动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毫不审视男性世界、决不把握男女关系局面的绝对被动者。她唯一的主动就是主动接受李主任的安排。
与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有所不同,王琦瑶以把自己物化为男性消费品为谋生手段时,并没有生存状况的残酷性在背后逼迫着。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维系基本的生存,而是为了追求平凡女性人生之外的浮华享受。这样,她的人生选择中就少了白流苏不得不为谋生而谋爱时的无奈和苍凉,而多了一份只有物欲、没有灵魂者的精明、虚荣和卑贱。同样,她也少了白流苏不断审视范柳原内心的平等意识、不愿堕为男人情妇的自尊自爱。
王琦瑶借蒋丽莉的家事来阐述自己的人生观时说:“你母亲是在面子上做人,做给人家看的,所谓‘体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重庆的那位却是在‘芯子里做人,见不得人,却是实惠。” 把妻子的名分看作是虚名,把做外室当作是女人的实惠,王琦瑶的人生选择中不仅放逐了人的尊严、放逐了爱情,也放逐了女人的现实名分,她抓得紧紧的只是黄灿灿的金条、只是那丰厚的物质利益。以美色谋生、以温驯邀宠,是王琦瑶的自由选择。这里,自由仅仅是自愿为奴的自由,违背了其维护人的主体价值的本意。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为白流苏、范柳原设置港战这样一个隔断现实瓜葛的特殊时空来激发他们的真爱,内中所含的价值尺度显然是认为合理的两性关系应该是超越现实功利的倾心相爱,尽管她几乎不相信这种爱在日常人生中能够实现。这其中就包含着隐含作者张爱玲对现实生存条件抑制理想之爱这一状况的质问、批判。然而,隐含作者王安忆在对爱丽丝风情的铺陈、赞赏中,恰恰认可了女性对物质利益的屈从、对理想爱情的放逐、对女性主体性的摒弃。“她们个个都是美,还是高贵,那美和高贵也是别具一格,另有标准。……她们的花容月貌是这城市财富一样的东西,是我们的骄傲。……她们是美的使者,这美真是光荣,这光荣再是浮云,也是五彩的云霞,笼罩了天地。那天地不是她们的,她们宁愿做浮云,虽然一转眼,也是腾起在高处,有过一时的俯瞰。虚浮就虚浮,短暂就短暂,哪怕过后做它百年的爬墙虎。”这便是隐含作者王安忆为王琦瑶这些自愿入笼、连名分也不要、只想着实惠的“金丝鸟”们所唱的赞歌。尽管以浮云和爬墙虎这两个意象概括、展望这类女性的生存状况中,可以看出王安忆对这类以美色谋生的女性的命运并不乐观,但是她最终在价值取向上还是理解了她们追求短暂浮华、不计长久人生、泯灭自我主体意识的思路。“王安忆对王琦瑶的命运充满了怜香惜玉般的同情,对她的风情之美又充满了赞美。”(5)理解、认同而不是批判、否定王琦瑶这种人生选择的隐含作者王安忆,也就放弃了悲悯女性生存无奈、关注人的主体性状况的精神高度。
三
隐含作者王安忆对王琦瑶的人生选择也不是全无反思的。李主任坠机而亡、时代变迁后,隐含作者借王琦瑶外婆的眼光怜惜地看着王琦瑶。“其实说起来,外婆要比王琦瑶更懂做人的快活。王琦瑶的快活是实一半,虚一半,做人一半,华服美食堆起另一半。外婆则是个全部。”这“全部”的做人的快乐——准确地说是做女人的快乐,隐含作者通过对外婆生命逻辑的理解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女人的美”,二是“女人的幽静”,三是“女人的生儿育女”。“女人的美”和“女人的生儿育女”,意思十分明了。“女人的幽静”,隐含作者借“外婆”的思路把它解释为女人“不必像男人,闹哄哄地闯世界,闯得个刀枪相向,你死我活。男人肩上的担子太沉,又是家又是业,弄得不好,便是家破业败,真是钢丝绳上走路,又艰又险。女人是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成了。”这三方面,作外室的王琦瑶缺的就是“生儿育女”的快乐,至于“女人的美”和“女人的幽静”,她和外婆是一样的。从外婆的视角看,王琦瑶享受“华服美食”,而不享受“生儿育女”的快乐,是“平常心已经没了,是走了样的心,只能领会走了样的快活。”这里,隐含作者王安忆显然是借外婆的立场对王琦瑶做“金丝鸟”的人生选择作出反思。
“生儿育女”的快乐是“有名有实”的。“实”是自然亲情,“名”是母亲的身份。被命名为母亲可以克服“爱丽丝”女人因没有名分而难以进入社会秩序的尴尬。相形之下,“美食华服”如过眼烟云,终是虚幻。无名的女人,再美也终是浮云,终要变成无奈的爬墙虎。隐含作者此时的立场显然与前面理解王琦瑶选择做爱丽丝女人的立场形成对话,一定程度上显出文本在价值指向上的多元性。但这个多元,显然只在女人到底应该选择短暂的浮华还是应该选择持久平常的欢乐之间进行换位思考,而始终没有思考无论是短暂的浮华还是持久平常的欢乐都以依附于男性为前提,始终没有对王琦瑶跪拜于男性权势之下、跪拜于金条面前的无主体性状态作出反思。“如果说文学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打破世俗等级规范加诸人类的物质羁束,代之以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有的精神平等与灵魂自由,那么王安忆的近年作品则表明她已放弃这一价值路向,转向了对世俗规范和现实秩序的认同。”(6)《长恨歌》正好映证了这一评价。
“女人的幽静”、女人的“无事一身轻,随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便成了”,是王琦瑶与外婆共同的欢乐,也是隐含作者认可的女人的欢乐。然而,这种欢乐,是奴隶的欢乐,是女人放弃承担人生的欢乐。对这种欢乐的认同中,隐含作者回避了人如何对待自我的问题,也回避了男女两性如何相互对待的问题。这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式的思路,并不追问女人放弃进入社会历史是否会带来压抑感、是否会带来主体被分裂的痛苦,并不追问是否每一个男人都愿意有福同享,并不追问是否每一个男人都值得有难同当。假想女人只要愿意放弃社会历史,便能“随着”男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显然是把男女关系简单化的见识。蒋丽莉的母亲没法拴住丈夫的身心就是最直接的例证。在女人放弃主体人格尊严、放弃社会历史便能“无事一身轻”的乌托邦想象中,隐含作者王安忆确实成了回避女性生存真相的“逃避者”(7)。
历尽沧桑之后,王琦瑶以朴素的形象出现在平安里。与康明逊恋爱,似乎是她从追求无名的浮华走向追求平常欢乐的开端。康明逊尽管是富家子弟、大学毕业生,但王琦瑶和他恋爱显然是基于两人的相知,并不是高攀富家以求浮华。康明逊的魅力在两方面,一是他在朋友圈中他处事大方,二是他理解、体恤了王琦瑶弱者自卫的小心眼。但他们两人有缘无分,只圆了一段野鸳鸯的梦,虽留下一个女儿,却没有让王琦瑶完全享受到外婆所说的“有名有实”、未失“平常心”的人生欢乐。这根本的原因是,康明逊那颗与王琦瑶息息相通的心,其实是弱者只能自顾自己、不能承担爱情的自私的心。因自己是妾生的孩子,自孩提时代,康明逊“他的一颗小小的心里,其实全是倚强凌弱,也是适者生存的道理。”“他和王琦瑶其实都是挤在犄角里求生的人,都是有着周转不过来的苦处,本是可以携起手来,无奈利益是相背的,想帮忙都帮不上。”王琦瑶虽是美色佳人,但因曾是阔人外室,按照世俗观念显然属于生命价值已经贬值的女人之列,不符合康明逊家庭对媳妇的要求。
所以康明逊只能对王琦瑶说“我没有办法”,“我怕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意思的是,王琦瑶对这种没有担当的男人却只有体恤,没有质问。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俩本都是不能承担自己人生的无主体性的人,所以,王琦瑶心中并没有人不应该向世俗低头的观念、也没有关于自我人格完整的观念,自然就不会去质问康明逊对家庭的妥协。“像我这样的女人,太平就是福,哪里还敢心存奢望?”这里,王琦瑶表达的不是对自己过去攀附男性的无主体性状态的反思,表达的恰是对世俗社会认为自己生命已经贬值看法的认同。这种认命的态度,展示的是主体再度沦陷的昏昧状态。它不可能使王琦瑶的生命迸发出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力量。它只能使王琦瑶由过去的凭色相而攀附浮华走向因屈从世俗而不敢奢求完整人生。体恤康明逊的王琦瑶仍然不是一个人格完整的、富有主体性的女人。她与康明逊的心心相印,不过是奴在心者之间的息息相通。她对康明逊的迁就、纵容,不过是女人自轻自贱之后的委曲求全、妥协退让。
权威叙述者和隐含作者怜惜王琦瑶这种妥协退让的态度,体恤她作为弱者在小处自卫的小心眼,却没有审视、否定她在自我生命价值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认同世俗观念的自轻自贱。这样,作品也就精神向度上向世俗观念妥协、达不到提升生命价值维护生命尊严的高度。
终其一生,王琦瑶在与相恋的男人的关系中,始终都没有建构出强健的主体意识。她不能以主体的尊严对待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以主体的责任要求异性。直至最后与老克腊相恋,她为维系这种关系所作的最大努力便是捧出那个装着金条的雕花木盒。她延续的还是以物质利益与青春情爱作交换的思路,只不过这时她已经转换成了付钱的消费者和乞求者。她致死也没有否定把人物化、把性爱物化的观念。此时,权威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尽管也通过间接引语让她直接向老克腊表达了自己的寂寞,但小说最后一章已经减少了王琦瑶心理描写的密度,也较少从王琦瑶的视角来叙述人事,而更多聚焦于老克腊的心理,更多从老克腊的视角来感受爱欲与年龄的冲突、感受王琦瑶的衰老以及与这个衰老不相协调的欲望。
这样,王琦瑶的寂寞和欲望,就显示出压迫老克腊心理的特质,显得既可怜又可鄙。叙述视角、叙述距离的这一转变表明,权威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已经拉大了与王琦瑶的距离了。但拉大距离之后权威叙述者和隐含作者所审视、否定的并不是王琦瑶物化的性爱观念,而是她的年龄衰老与美色衰退,因为叙述者所依赖的视角人物老克腊觉得自己与王琦瑶的距离只在于其年龄衰老与美色衰退。老克腊最后一次离开王琦瑶,“有一种死到临头的感觉”,不过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时空上“没赶上那如锦如绣的高潮,却赶上了一个结局”,并不是因为他觉得王琦瑶物化的情爱观念有什么不对。总而言之,叙述者既没有让老克腊对王琦瑶物化的性爱观念作出审视、批判,也没有超越人物视角对王琦瑶物化的性爱观念做出否定性评论。
以美色作为生命资本的王琦瑶,终因年老色衰被隐含作者和权威叙述者抛弃了!小说的结尾,叙述者还通过长脚的视角加强了对王琦瑶年老色衰的厌弃态度:
“这时他(指长脚)看见了王琦瑶的脸,多么丑陋和干枯啊!头发也是干的,发根是灰白的,发梢却油黑油黑,看上去真滑稽。”在年老色衰方面厌弃王琦瑶,而不反思王琦瑶把性爱物化的人生观,隐含作者在此时再次现出了其生命观念的庸俗。
四
《长恨歌》文本中,王琦瑶真正富有精神向度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不畏忌世俗观念,以独身女人的身份生养了女儿薇薇;一件是与程先生的关系中不混淆恩义与情爱的界限。决定把女儿薇薇生下来,是因为王琦瑶在去医院的路上想到,“她其实什么都没有。连这个小孩子也要没有了,真正是一场空呢!”留下肚里的孩子,是她正视自己的生存境遇后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承接了外婆关于女人“生儿育女”的快乐的人生观,而剥离了外婆关于女人依附于男人随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人生观,同时还对抗了世俗观念对单身女人的性爱限定,因而包含着精神自主的内蕴。然而,隐含作者在这一件事的叙述中,却尽量回避了王琦瑶与世俗舆论必然有的冲突。权威叙述者强调平安里的“经验丰富”、强调平安里女人对王琦瑶的“艳羡”,这种对弄堂舆论的简单化想象,在最大限度内保全了王琦瑶与世俗民间社会的和谐,尽量消解了王琦瑶这一行为对抗世俗的意义,从而在艺术表现上尽量抑制住王琦瑶在这件事上所达到的主体自强的精神力度。
与程先生结婚,本是王琦瑶后半身最实惠的选择。但在孩子的“满月酒”上,“程先生听她只说恩义,却不提一个‘情’字,也知她是借了酒向他交心的意思,……”。严格区分恩义与情爱,王琦瑶尊重了自己内心的情爱感受,也对程先生做到了坦荡无欺。王琦瑶此时在处理与程先生的关系上,显然完全不同于面对李主任时以恩义统一情爱的实惠态度,完全不同于对待萨沙的欺诈态度,也不同于自己在“上海小姐”时代把程先生作为“垫底”的功利态度,而显出超越世俗功利的精神风骨。然而,不久,隐含作者又让王琦瑶摸着那个装着金条的木盒“感伤地想:她这一辈子,要说做夫妻,就是和李主任了,不是明媒正娶,也不是天长地久,但到底是有恩有义的。”隐含作者让王琦瑶在处理与程先生的关系来一个短暂的精神超拔之后,又让她迅速回归到了固有的实惠至上的两性关系立场上来。
总之,《长恨歌》书写王琦瑶这样一个不关注社会历史的女性的一生,小说在总体价值取向上屈从于以色相美的等级来衡量女性生命价值、以世俗的精明来睥睨生命诗意的世俗观念;在探讨女人的人生道路方面,作品徘徊在女人到底应该追求浮华还是应该安分守己这两端,总体上是体恤了女人为了物质享受出卖情色的精明、卑贱,并不反思女人把自己物化的自轻自贱。王琦瑶短暂的两次精神自强和人格自尊,因为她自己的迅速回归和叙述者的抑制性表达,终未能构成小说的精神突围。作品在总体价值取向上是放逐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这样,《长恨歌》对王琦瑶独特女性世界的书写,不仅没有以女性的生命尊严质问、颠覆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反是以女性风情的充分舒展,强化了女人是男性世界情色点缀的观念,加固了男权文化物化女性、奴化女性的观念。尽管就题材而言,《长恨歌》确实另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其间作家对世态人情的把握亦卓富才情。然而,它终不过是一个阉割女性主体性的文本。
(1)“即述即议”是徐德明在《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中对王安忆叙事特征的总结,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李静在《不冒险的路程——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中曾指出王安忆的写作有一种“社会生物学”的视角,见《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
(3)王晓明在《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中评价王安忆的创作说“在她迄今为止所有描写上海弄堂生活的小说中,你几乎都能看到这种混合着欣赏和挑剔的笔致。惟其欣赏,她每每能写出别人不容易体会的诗意,又惟其挑剔,繁密的叙说就不至于越走越浅,总能保持一定的深度。我觉得,往往正是这些混合型的描写,构成了她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 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4)郑文晖:《王琦瑶身后的文化说明了什么?》,《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5)郑文晖:《王琦瑶身后的文化说明了什么?》,《文艺争鸣》2004年第6期。
(6)李静:《不冒险的路程——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
(7)李静在《不冒险的路程——论王安忆的写作困境》中说:“看得出,王安忆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的重重包围下一直作着可贵的突围努力而逐渐走向经典化,但我却认为她成为了一个‘逃避者’。”见《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
(编辑:魏巍)